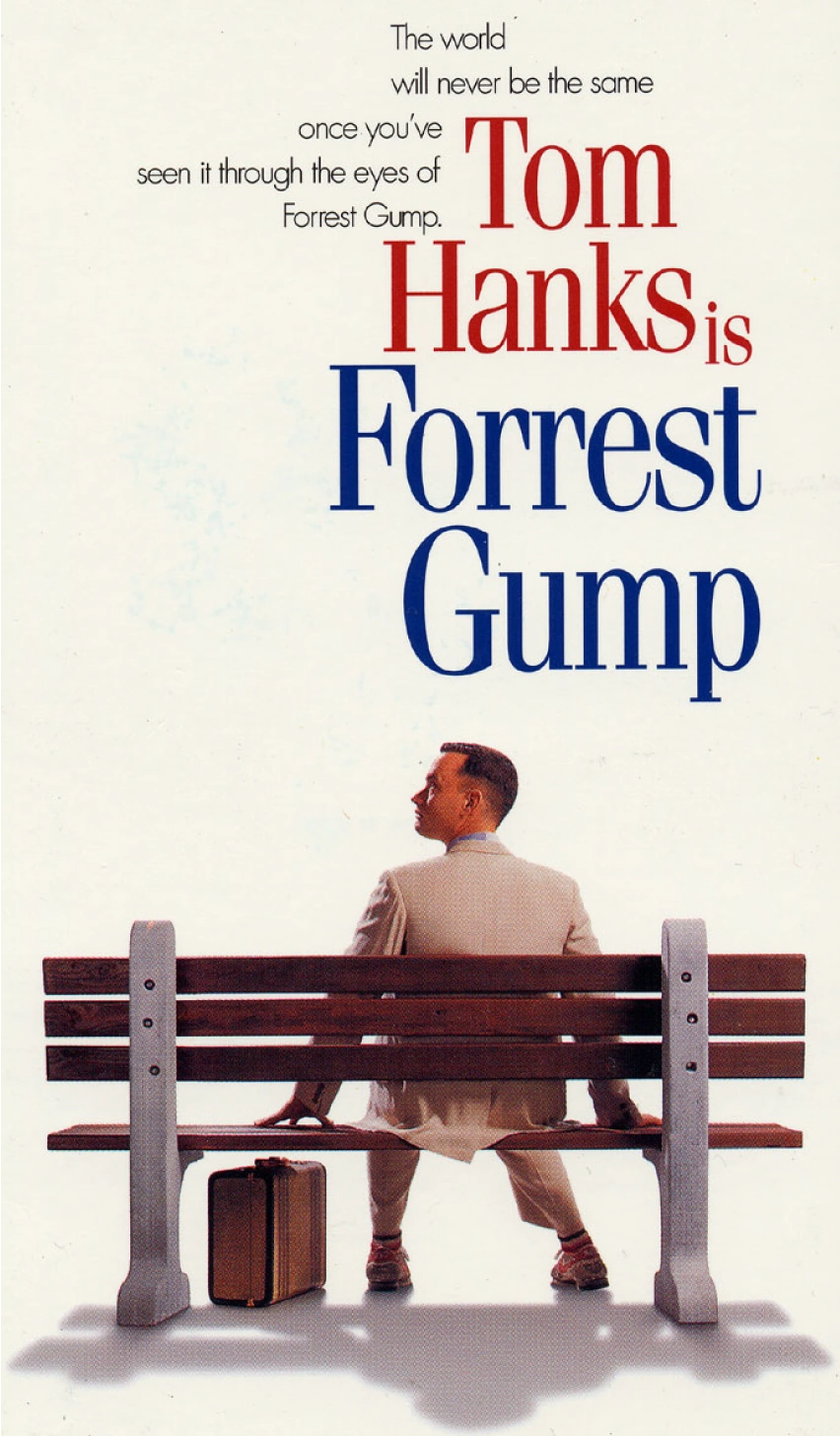(原载2016年4月《联合早报》。)
(今年第六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筹委会刚刚在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,明天就公布完整片单。我也从今天起开始陆续整理过去三年来为电影节写的推介影话,回顾一下这一系列电影节的辉煌灿烂,并期待再攀高峰!)

去年的第三届新加坡华语电影节,放映回溯台湾电影50年的纪录片《那时此刻》。导演杨立洲受访时提起1976年刘家昌执导的《梅花》,抗日义士被绑赴刑场的戏,看在咱们眼里,矫情、造作得令人笑掉大牙。可《那》片在回顾了这场戏之后,切到三名老兵通过平板电脑看《梅花》而老泪纵横的纪录片画面,让荧幕下身为纪录片观众的咱们蓦然发觉,我们有什么资格笑人家?我们不曾生于忧患,不懂他们曾经的热血与至今抹不去的悲怆。或许,某一个特定的群体之所以会着迷于某个剧种(如今天的韩剧迷),正是因为这类影剧正好弥补了他们心灵中的某一个缺口,给了他们一个宣泄的管道。
老兵的眼泪启发了杨导,把《那》片的取向改为各个时代的影迷的视点,虽仍是电影发展史的内容和结构,但主角不再是电影本身,而是随着台湾的时局起伏而欢喜悲忧的影迷――这是台湾电影
“写给影迷的情书”。
或许是《那》片给了节目策划灵感,即将在本月底开幕的第四届华语电影节,更为本地观众奉上“话说华语片”单元,展映八部纪录片。这里拿其中四部来谈,恰好是以四种不同的视角来创作的纪录片。
最接近《那》片的“时代变迁下的影迷视角”的纪录片,应是《声光转逝》。旧金山唐人街里从演出粤剧到
“进口”两岸三地华语片的剧院,见证百年华人移民的流光故梦。片中几位老华侨受访,讲述小时候被父母亲带进剧院看粤剧演出,大人看得入神,孩子们却在走廊上嬉闹着,只有武戏才吸引他们的注意。这些受访者在忆述这些半世纪前的往事时,眼里焕发出兴奋的神采――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戏曲或电影情节,看了多少、记得多少已不重要;最美的回忆是剧场、影院当下的氛围。
但对大人来说,影剧的内容才是他们的慰藉。战前第一代移民遭遇政府排华,多无法把家眷带来美国,一踏出唐人街又遭到歧视;而戏曲和影片成了孤独的人儿情牵故土的一条线,让他们难得看到影剧作品对华人的正面刻划,宣扬宽容、坚忍、遵纪守法、积极向上、对家庭负责的价值观。
第二代移民在意识形态的矛盾高涨之际,对自己的华裔本位有更深刻的觉醒。男青年对《龙门客栈》、李小龙电影等华语动作片趋之若鹜,不少还到精武体育会学武;而好莱坞电影《西城故事》(West Side Story)也启发他们要团结起来,因应种族偏见。女青年则或许在求学时面临“长得不如白种女同学漂亮”的自卑心态,可眼看郑佩佩、萧芳芳在时装片里把A字迷你裙、阿哥哥舞靴穿得酷斃了,而确立了华裔女孩的身份认同。电影隐隐给他们带来了身为华人的自豪感。
同是影迷视点,大不同的是《侯孝贤画像》,一个“小”影迷对偶像导演的近身观察、理解、感受他的人生。此影迷也不算小,是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(Olivier Assayas)――此片完成于1997年,是这位似乎深深迷恋东方影坛的导演跟张曼玉结婚的前一年。透过他的半自传电影《童年往事》,我们对𠉀导的童年已了解甚多。但《侯》片让侯孝贤带着咱们重访他在高雄的童年足迹,看他跟孩提老友偶然重逢时的互动;或是彳亍在旅游开发正进行中而逐渐“失真”的九份;抑或在KTV里豪气高唱《跟往事干杯》……一切如同《童》片中老祖母拖着佝偻的身影,在小镇的路上声声呼唤玩到不知回家的小侯孝贤:“阿孝咕……阿孝咕……”我们透过电影了解侯导的美学思维及思想面貌,而《侯》片更寻觅、还原了侯孝贤这个现实中的草莽老顽童,让他在阿萨亚斯的镜头里鲜活起来。


但是,对于一位曾被时代忽略,而今大家只恨对她了解太少的电影人,只好用带有侦探、报导文学味道的《金门银光梦》来进行时间与空间的拼图。连提及一些战前旧金山华裔影人的《声光转逝》里都没提到伍锦霞(《金》片正好补叙了《声》片的一块缺口),竟是华人影坛中的第一位女导演、第一位(在21岁时就)进军好莱坞的华人导演。李小龙的第一部电影,就是伍锦霞合导的《金门女》(当时李还是个婴儿)。
《金》片导演魏时煜重新寻访伍导一生走过的轨迹,从旧金山到香港,从洛杉矶到夏威夷到纽约。伊人已逝40年,魏导无法像阿萨亚斯一样对侯孝贤贴身追访,只能从残存旧剪报和影像资料,加上她的胞妹、过去的合作对象、影迷、故人之女等对他们口中的“霞哥”、“霞叔”的描述,重构这位外表阳刚(是她的本性--包括女同志性向使然?还是为了在片厂压得住一众男性演职人员?)、内心澎湃而善感的知性导演的生命图谱。

若说《那时此刻》、《声》片和《金》片所提及的,都是蓄意“与观众寻找对话的频率”,因而能直接打进某些特定背景的观众心坎里的主流电影,与之强烈对比的便是《那日下午》。蔡明亮,和他的缪斯李康生,素来就死不随波逐流、讨好主流观众,而坚守他们那种“我就是要你走进我的世界”的创作取向和美学风格。
在《那日下午》里,蔡李两人促膝长谈,在蔡导新买的废屋中架起摄影机,穿着拖鞋坐那儿聊了两小时,聊作品、聊人生历程和𫐶事、聊两人的一世情谊。蔡明亮说他们的电影就爱拍废墟,连这出纪录片也在废屋里拍;聊着聊着,就如同我们细细品味他们的旧作一般,身为观众的我们或会慢慢发觉,他们再三通过作品(包括这出纪录片)引导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里的废墟,其实就是普罗都市人内心中的废墟,咱们享受着表面光鲜、幸福美满,却在潜意识里有对现实的犬儒、洪荒和虚无感而往往不自知。《那日下午》的主角,看似不是
“影迷们”,而是蔡李本人;可实际上,他俩是“都市人们”的代表。

顺便请读:
我家的天堂乐园(在老家麻坡的观影记忆)
电影人与人间的促膝长谈(香港纪录片《想像易文》、短片《海滨薄梦》;大陆电视电影《温水蛤蟆》)